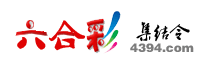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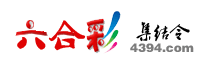
惨剧就是这样发生了!
三石榴岗子村 中国---赵想睡了,但她的丈夫想看电视。就是这样简单的事情。
按照赵的说法,这对中国河北的贫穷农村夫妇过去没有吵过架。但在这个九月的温暖夜里,谁也不愿意妥协对方。于是34岁的赵,撇下同一床被子底下的丈夫与两个幼小的儿子,走出门外,抓起窗台上一瓶农药。
“ 我刚刚喝了一点点,但农药象是把嘴和喉咙烧着了,”赵说。这个普通农妇除了要耕种庄稼、照顾丈夫和两个男孩(一个5岁,另一个10岁)以外,还得维持一个 7口之家的日常生活。“我当时也没有往深里想。刚刚想到这样做不对,就随随便便地喝了农药。我没想到两个孩子,哪怕是一点点。当时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
赵的这种绝望情绪看来在农村中国十分普遍,尤其是在女性当中。她们中的许多人独自肩挑整个家庭的生活重担。在她们眼里看来,逃离这种生活的办法通常唯有一死。
中国女性的自杀率高出男性25%,而农村的自杀率则是城市的3倍。研究表明,西方男性的自杀率通常至少是女性的2倍以上,有时甚至达4倍之多。但是在中国,尤其是农村年轻妇女,这一数字令人揪心。
这些自杀的女性多数为赤贫,她们不顾一切的自绝行为提醒人们社会不平等现象仍在困扰中国,提醒政府在提升农村生活标准的努力上还有诸多难题。尽管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很快,但农村妇女一直被人遗忘,她们得面对那些看来无法逾越的阻力。这些阻力多半来源于一种传统观念:妻子们在家庭中的地位是低三下四的,是从属的。
“她们对生活的巨大冲击,比如家庭冲突和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还没有准备。”金晓(说)。金晓是湖南省某个社团的研究人员,他们的工作致力于预防年轻农村女性自杀行为。“大多数自杀的女性没有受到什么教育,挣得很少,受制于过去中国的传统思想非常明显。”总的来说,中国的自杀率相对较高。附属于回龙观医院的北京自杀行为研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表明,中国每年约有287,000人自杀,发生率约为十万分之23,这一数字是美国的两倍。多年来中国人的自杀率基本保持稳定,但研究人员称,现在有更多的类似前文提及的赵姓妇女的冲动型病例,此外,更多更为年轻的妇女在试图自杀。北京自杀行为预防中心于2002年的研究发现,尝试过自杀的年轻女性通常在学校接受教育的时间只有5年,其家庭的人均月收入仅13美元,低于国家平均水平。多数受访者诉说有不幸福的婚姻,超过42%提及经济困难,超过38%的受访者说丈夫曾打过她们。该研究还表明,“最显著的特点是,家庭纠纷占到自杀起因的绝大多数。”“以前,多数年龄段处于30至50岁,现在则是15至34岁”,许荣(音)说。许是北京一家非赢利机构的项目经理,负责帮助农村女性。“无论在何时,一旦她们的梦想与现实不能达成一致,加上如果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她们就会想到去自杀。”在赵的这个事例当中,婆婆听到隔壁的吵闹声奔出门外,正好夺下儿媳嘴边的农药瓶子。但农药中毒反应已经发生;为此,家庭不得不借债以支付医院方面的费用,它占到了整个家庭年收入的三分之一。“我很生气,一天到晚在田地里累死累活,(他要看电视,使我)我睡不着”,赵说。因为自杀是件不光彩的事情,赵请求不要提及她的全名。“农村妇女们愤怒时喝农药的情况很普遍,我从来没有想过丢下丈夫,可我又能往哪儿去?”喝农药自杀方式在中国农村很常见,这种化学品很容易得到。研究显示,58%的中国自杀案例是使用的农药。“尝试自杀与最终完成自杀者的比例约为10比1,如果所进行的方式是最为致命的那种,则该比例还会更高”。北京自杀预防组织的执行主任麦可.R.菲利普斯说。近年来,北京官方已将自杀行为确认为重要事务,并给予经费用于相关研究支持,但目前为止还未形成一个全国性的计划或政策来对此进行干预。虽然政府的行为缺位,但已有数家农药厂商将其产品小包装化以及加上锁扣等装置,使得农民不象原先那样容易地使用农药进行自戗。与此同时,一些非赢利组织还在某些小山村如三石榴岗子村和东浩村(音)等开展项目教育,并取得进展。东浩村位于北京西北,仅3小时车程。许荣的机构“农村女性文化发展中心”,将山村里“有麻烦”的村民以及当地的一些干部带回北京,教导(他)她们如何变得更积极,比如教她们跳扇子舞来取代原先的麻将。他们希望此举可以给妇女们某种生活目的感,并由此遏制自杀潮。“几年前,我们这每年都有人自杀。现在少多了,我们有了更多的娱乐方式,比原来更快活一些。”孙江保(音)说,他生活在三石榴岗子村。孙的妻子赵海霞(音),在10年前的春节自杀。春节虽说是一年里最重要的节日,但也是家庭纠纷好发的时节。孙与妻子的争执十分典型。孙说,他患有肝炎,而妻子让他休息,不要再回北京火车站做搬运工。“她不让我出去工作得那样辛苦,让我呆在家里休息,”孙说,他在北京挣的钱要比在家里田地里的收入高将近70倍。“我对妻子说得去火车站签下年度的用工合同,签完之后就回家,但她不相信。”孙的妻子喝了盐卤,这是一种很多农家随手而放的苦味液体,用来将黄豆汁凝成豆腐。“当我发现她时,她就躺在这张床上,旁边有个碗,”孙回忆道,“碗底是黑色的,她望着我说'从今以后,你要照看好我们的孩子。'”在东浩村,一位不愿透露全名的王姓妇女说,她曾经3次自杀,她说丈夫一再虐待她。45岁的王说,“总是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我不记得他打过我多少次了。每天我都不高兴、烦燥,觉得生活没有意义...你看看我手上的这些疤痕,这些都是他拿棍子打的。”在西方,医生可能对王的抑郁症进行治疗,并鼓励她脱离这种虐待的夫妻关系。但在中国,医生和自杀行为干预者们忽视了此种精神疾患,而将精力集中于改善家庭条件。49岁的李桂明(音),是当地的一名村干部,帮助王并后来将她和一些其它人送到北京接受指导。他认为传统的性别角色(歧视)在农村还广有市场。“女人自打她们生下来以后就低人一等,”李说,“要是你生了个女孩,别人会说你生了破丫头;如果生了男孩,他们会说你得了个大胖小子。”王说丈夫骂她时她已经无动于衷,于是俩人的争吵变少了。她帮丈夫每周四次在市场上卖皮带、袜子和帽子,可以(比干农活)挣更多的钱。王说丈夫年纪大了,脾气也温和了一些,现在不再打她了。时至今日,因为当初看电视而发生争吵进而试图自杀的事情已经过去了7个月。赵坚持说,她不知道农药是致命的。但另外,她又说曾准备好去死,不是吓吓丈夫闹着玩的。尽管自杀行为干预者们一直帮助村民们勇敢地谈出她们的问题。但赵说,这样的谈话不合常理。“我在村里有朋友,但不愿将我的不快活告诉她们。你也不会把你的糗事告诉邻居们,”她说,“人们看不起那些自杀的人,她们被认为是失败者。”至于将来,她说,不会再自杀了: “我不会再那样做了,我们浪费了好多钱,大儿子10岁了,我得攒钱为他将来盖房子。”
上一篇:反击:骂福建人起源,张一一不说人话
下一篇:变味的同学会,带给我什么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