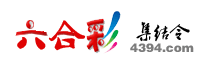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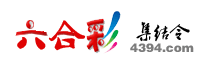
4月12日美国《侨报周末》刊发题为《在中国,寻找“科学”》评论员楠石因的署名文章,指出:中国许多技术发明的后面,缺少了西方科学史上那种特殊精神,即长期而系统地通过数学化来探讨宇宙的奥秘。如果中国科学沿着自己原有的轨道前进,无论如何加速,也不可能脱胎换骨。对此,我有同感,正如我在重要的不是“嫖宿”的解读,而是“幼女”的定义一文后记中写到:在国际政治的政治心理学范畴,有一个“世代政治论”。根据学者杰维斯 (Robert Jervis)的《国际政治的知觉与错觉》,一个人的政治观,最容易被他的教育、家庭、成长时的国家背景、以及他第一次直接参与的群众运动影响,因为那会成为心理的长久烙印。参阅:从中国人怎样才高兴?谈中国不高兴又如何?好像扯远了,转载如下:
一、中日经济差距到底有多少年?
这是个由来已久的话题。2001年的时候,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的关志雄先生说至少40年;笔者认识的一位日本经济学教授在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后感慨地说:“说差距有100年有些夸张,差距有50年有些保守,应该差距在80年左右吧!”作为经济学家,会通过GDP、平均寿命、婴儿死亡率、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城市的恩格尔系数和人均电力消费量等方面的各项数据进行科学分析后得出自己的结论。但笔者想从科技的角度来探讨一下。
近日,在大阪举行的第六届中日经济研讨会上,广汽老总张房有骄傲地宣布“广汽已经成为本田最优秀的海外工厂”。丰田和中国企业的合资,正是中日互补的典型模式。在热火朝天的建厂、造车、卖车后,在中国工人的辛劳后,利润大都流向日本,中国不过赚了一点可怜的加工费。当然,中国是“世界工厂”早已不是什么新闻,这个地位并没有多少值得骄傲之处。中日处在产业链的不同位置,两国经济界人士都非常清楚。中国社科院日本所研究员丁敏女士和笔者聊天时说,日本掌握的是核心技术,我们处在边缘,我们挣的是打工钱。
为什么我们处在边缘,主要原因之一是不掌握核心的、先进的技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一条永恒的真理。资源短缺、国土狭小的日本,发展到今天靠的是技术领先。业内人士常说,美国人掌握标准,站在最高端;日本人掌握技术,站在中间;中国人有得是力气,只好在底端干苦力。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企业缺少资金、技术和管理,于是采取拿来主义。最具典型的是汽车业的“以市场换技术”,结果市场给了人家,技术却没学来。
技术方面差多少,举几个例子就清楚了。中国准备建造高速铁路,就引进法国的TGV还是日本的新干线而热烈讨论。可别忘了,新干线是日本20世纪60年代发明的技术;广汽集团先后和丰田、本田合资,而这两家日本企业起步时,中国全国人民支援一汽,如今双方却完全不在同一档次上竞争。再想想丰田上百款车型的技术储备,差距之大不能忽视。数码产品方面,更是日本技术独步天下,热衷于抵制日货的人买数码相机、数码摄像机时大都会碰到这样的尴尬:没有国货可以替代,除非你不买。
在日本大阪的松下展示中心,有100寸的液晶电视;如果石油价格飞涨,丰田的燃料电池汽车会迅速占领市场;在神户,政府耗资上百亿日元进行基础研究,向医疗尖端领域进军。这绝不是给日本企业做广告,他们靠着技术领先,站在产业的上游,和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形成互补。按照日本企业界人士的逻辑,随着经济全球化,开展商务活动时单靠一个国家能力有限,应当以国际分工方式来提高生产能力,中国是日本最好的国际分工对象。将这段话拆开解读,无非是说“中国人是日本最好的打工仔”。
对这种流行已久的国际分工论、比较优势论,应该仔细分析。关于这个问题,我赞同钟庆先生《刷盘子还是读书》一书的观点:知识和技术才是宝贵的财富,是民族安身立命之本。气派的摩天大楼、轰鸣的制造工厂和耀眼的GDP不是根本,因为高楼大厦可以被地震毁掉,海外投资随时可能撤走,工厂也可以迁移,技术,拥有技术的人,拥有这些人的国家,才是最具竞争力的。回到开头的问题,中日经济到底差距多少年。笔者认为至少50年,因为技术差距至少50年。技术的差距,就意味着经济的差距;技术水平赶不上去,就难免处于给人“打工”的地位。
日本的大公司重视研发,和日本的国家产业政策息息相关。二战后,日本汽车工业起步时,也曾有过引进还是自己研发的争论,最终在国家产业政策的扶持下,日本的汽车产业坚持自主发展的道路,重视技术,走到了今天。除了公司的投入,国家也一直保持对科研的高投入。据了解,日本的科研投入占GDP的3%左右,处于世界领先位置。从今年4月1日开始,日本推行为期5年的日本第三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国家总投资额为25万亿日元。
技术差距大,于是中国的企业在有了钱后决定购买。然而,日本永远不会把核心技术、先进技术卖给中国。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的家电企业有个不成文的约定,向中国出口技术时,保证日本的技术至少领先20年。经济会全球化,但技术不会。一位日本企业家说,技术是我们的命门,不会轻易卖出去的。和中国打交道时,日本(包括美欧)动辄提知识产权问题,这表明了他们对此的重视。可以给你投资,用你的土地,用你的人来生产。可以在你的市场销售,但对不起,我的技术不能给你。你要偷偷学,好,法庭上见。
对此,中国政府审时度势,提出了“十一五”期间“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目标,一些企业也意识到加强研发的重要性。据报道,日本eAccess株式会社CEO千本癰夫在2006中日经济研讨会上,对华为公司大加赞赏,认为他们的技术要超过朗讯和摩托罗拉,并介绍了他们公司使用华为公司提供的技术的例子,令在座的许多日本人感到吃惊。但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和日本的科技水平整体差距还很大。要想赶超日本,我们还需要很多年,甚至几代人的努力。(作者:王冲 美国国务院访问学者,中国社科院日本政治中心特约研究员)
二、在中国,寻找“科学”
在那里,有一片古柏。利玛窦,汤若望,六十多位传教士长眠于此。在北京车公庄一所学校的后院,他们列队而立。春天的寒风,呼啸地穿过了那片古柏。
明朝末年,由于利玛窦的到访,拉开了西学东渐的帷幕,近现代科学第一次叩响了中国的大门。徐光启曾由利玛窦口授,译出了《几何原本》前6卷。然而,徐并未就此止步。在比较中国《九章算术》与西方数学之后,他直言:“其法略同,其义全阙。”陈方正先生的近著《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对此的解读是:“中国与西方数学的根本差别,即前者只重程序(即所谓‘法’),而不讲究直接、详细、明确的证明(即所谓‘义’)”。
继徐光启之后,冯桂芬深入研究西方数学,所获心得是:“数学为西学之源头所在,格致诸学皆由此出”。李善兰在译完了《几何原本》余下的9卷后,着手翻译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他感慨系之:数学“可以探天地造化之秘,是最大学问”。这是中国学人迟至19世纪中叶之后才对数学在西方科学传统中的至尊地位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余英时语)。
实际上,利玛窦带来的《几何原本》,为中学西学“科学”传统的“分途”(separate paths)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标识,也为人们重新思考著名的“李约瑟问题”(The Needham question)留下了历史样本。英国学者李约瑟写下了煌煌7卷本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用大量史实证实他关于“中国有科学”的论断,但在1954年、1969年、1990年,他三次提出思之久矣的困惑:16世纪之前中国在科技发展许多方面超过西方,何以现代科学崛起于欧洲而非中国?这就是至今让人争论不休的“李约瑟之惑”。
1975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李约瑟曾与余英时对谈,余英时讲到冯友兰早年的那篇《中国为何没有科学?》的英文文章,李约瑟立即说:“冯的问题提错了。中国缺少的不是科学,而是现代科学。”前些时候,余英时为陈方正新著撰文,旧事重提,指“李约瑟问题”根本不能成立,因为“中、西这两种‘科学’同名而异实”,“中国许多技术发明的后面,缺少了西方科学史上那种特殊精神,即长期而系统地通过数学化来探讨宇宙的奥秘”。余先生坦率地说:“中国科学从未走上‘数学化’道路,其事昭然”。他甚至断言,“中国科学”如果沿着自己原有的轨道前进,无论如何加速,也不可能脱胎换骨,最后与“数学化”为特征的西方“现代科学”融合成一体。
那么现代科学何以出现在西方?它的源头可能只有一个,即来自于古希腊的科学传统。早在16、7世纪西方“科学革命”之前,古希腊的柏拉图即受到毕达哥拉斯教派对于数学“无上重视”的深刻影响。柯林武德(R.G.Collingwood)在《自然的观念》一书中将其誉为“自然科学中的毕达哥拉斯革命”。这个“革命”的本质,即在于运用精确的数学以量化自然界的研究。1953年,在给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斯威策(J.E.Switzer)的信中,爱因斯坦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以及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以找到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
上述的看法是不是西方中心论的偏见使然?至少1600年以来的历史事实是确凿无疑的,“科学革命”并没有在中国发生。其中的原因,也不仅仅在“数学化”(mathematicization)这一个支点上。一般认为,文化专制、商业落后、观念封闭、缺乏理性精神,是中国难以实现“科学革命”的一座座围墙,而开放的政治经济制度和观念形态与科学的发展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它们是科学发展的“助产士”,也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推进器”。
回想“五四”运动以降,“赛先生”得到中国学人的炽烈欢迎。90年来,“现代科学”在中国得以逐步昌明。但言及科学传统、科学精神,中国人也可能还需要从“现代科学”的本质含义中去寻找“六合之外”的力量。庄子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是指,天地四方。庄子之论2000年来对中国学人的求知取向影响甚巨。朱熹自记说:“某五六岁时,心便烦恼:天体是如何?外面是何物?”余英时评论说,可见朱熹的好奇心“最早是从‘六合之外’开始的”。
站在利玛窦的墓前,风很大,打得古柏一摇一摇地。那风应当是来自“六合之外”的。“天体是如何?外面是何物?”也许,中国科学的发问终究不能只落在“六合之内”。
点评:难道说,百年以来,我们深信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错了?应该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换言之,“中学”什么为体,“西学”什么为用!或“西学”什么为体,“中学”什么为用!如,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仅是一种思想、一种学术,甚至为非主流观点。但到了中国,就成了真理,而且还是普遍真理,好像有放置世海的“普世价值”。这科学吗?这是科学发展观吗?难道,马克思已经“中国化”了?成为新儒教与官僚,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和政治体制?正如我评《新儒林外史》:鲁迅喷毒熏倒马克思的观点:当今“国际竞争的核心不是资金和人才的竞争,也不是技术的竞争,而是制度的竞争。从中国长远来看,应该学习的是制度改造。”这才科学,这才是科学发展观!